戰略規劃讓企業在今天開始做迎接未來的準備它要問的是:“我們的事業應該是什么?”它要問的是:“我們今天必須做什么才能擁有未來?”戰略規劃需要做出有風險的決策,需要有條理地舍棄過去,需要對創造預期中的未來所需的工作進行明確的界定和分配。戰略規劃的目標是立即行動。
01
戰略規劃不是什么
管理者有必要弄清楚戰略規劃不是什么。
??? ?1. 它不是一個魔術箱或者一堆技術。它是分析型思維,是把資源投入到行動中去
在戰略規劃過程中,可能要用到許多技術,但沒有哪一種技術是必不可少的。戰略規劃可能需要使用計算機,但最重要的問題,“我們的事業是什么”或者“它應該是什么”,是無法量化并編出計算機程序的。建模或者模擬可能有幫助,但它們并不是戰略規劃,只是用于特定目的的工具。對于某個特定場合,它們可能適用,也有可能不適用。量化不是規劃。誠然,在戰略規劃中,哪怕只是為了肯定沒有自欺欺人,人們也應該盡可能地使用邏輯嚴密的方法,但是有一些最重要的問題也許只能用定性的詞來表達,例如“較大”或“較小”,以及“較快”或“較遲”。這些詞是不便于用定量技術來處理的。還有一些同樣重要的領域,例如政治風氣、社會責任或人力資源(包括管理資源),是根本無法量化的。它們只能作為限制條件或邊界,而不能作為方程式中的因子。
戰略規劃不是科學方法在商業決策中的應用,而是思考能力、分析能力、想象力和判斷力的應用。它是責任,而不是技術。
?2. 戰略規劃不是預測。它不是設計未來。任何設計未來的企圖都是愚蠢的,因為未來是不可預測的。試圖設計未來,只會讓我們懷疑自己正在做的事情
如果還有人抱有幻想,認為人有能力預測很短的時間以后的事情,那么不妨看一看昨天報紙上的頭條新聞,然后問一問有哪些事情是誰能在十年以前預見的。我們首先必須接受一個前提——預測這種人類行為是很不準確的,而且只要超出一個極短的時期,預測就毫無價值。戰略規劃之所以很有必要,正是由于我們無法做出預測。
說明預測不是戰略規劃的一個更有力的理由是:預測總是試圖找出事件發展的最可能途徑,或者最好是一個概率范圍。但是,創業問題是一個將會使可能性發生變化的獨特事件。創業世界不是一個物理世界,而是一個社會世界。事實上,創業的最核心貢獻就是推動一個獨特的事件或者開展一項獨特的創新,從而改變經濟、社會或者政治情況。這一貢獻本身得到的回報就是利潤。
施樂公司在20世紀50年代開發和銷售復印機時,就是這么做的。經營活動房屋的創業者在60年代也是這么做的。當時,拖車成為一種新型永久性固定住房,幾乎占領了整個美國低價住房市場。50年代,雷切爾·卡森(Rachel Carson)的著作《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出版,這個獨特的事件改變了整個人類對環境的態度。在社會和政治領域,這正是民權運動領袖在20世紀60年代所做的,也正是女權運動領袖在70年代初所做的。
由于創業者會打亂各種預測賴以立足的概率,因此對于那些試圖為組織指明未來方向的規劃者來說,預測不能幫助他們實現目的;對于那些想要革新或者改變人們工作和生活方式的規劃者來說,預測也沒有多大的用處。
?3.?戰略規劃所涉及的不是未來的決策,而是當前決策的未來性
決策只存在于當前。戰略決策者所面臨的問題,不是所在組織明天應該做什么,而是要回答:為了迎接不確定的未來,我們今天必須做什么事情?當前的思考和行動中必須包含什么樣的未來性,我們必須考慮什么樣的時間跨度,我們現在如何運用這些信息做出合理的決策?決策是一臺時間機器,把大量不同的時間跨度同步為一個時間——現在。我們直到現在才開始了解這一點。但是,我們還是傾向于為未來決定要做的事情進行計劃。這可能很有趣,但是毫無用處。我們只有現在能夠做出決策,但是我們在做決策時不能只是為了現在。最權宜、最機會主義的決策,且不說那種根本不做決定的決策,可能會束縛我們很長時間,甚至永久地和無可挽回地束縛我們。
?4.?戰略規劃不是完全消除風險的企圖
它甚至不是一種使風險最小化的企圖。那樣一種企圖只會導致非理性和無限制的風險,并且必然導致災難。所謂經濟活動,就是把現在的資源投入未來,也就是投入極其不確定的期望中去。經濟活動的本質就是承擔風險。一種重要的經濟理論貝姆-巴威克定律(Boehm-Bawerk’s Law)證明:只有通過更大的不確定性,也就是更大的風險,現有的生產資料才能產生更高的經濟效益。
02
戰略規劃是什么
我們現在可以嘗試著給戰略規劃下一個定義了。戰略規劃是一個包括以下工作的持續的過程:系統地做出承擔風險的當前決策,并盡可能了解這些決策的未來性;系統地組織落實這些決策所需的努力;通過有條理的、系統的反饋,根據當初的期望對這些決策的結果進行衡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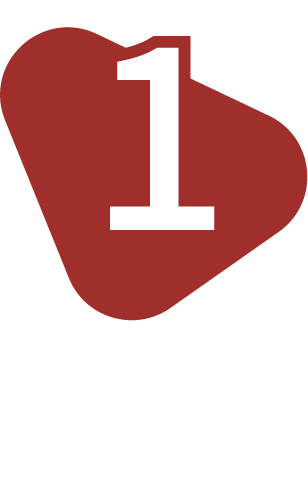
舍棄過去
做規劃要從企業的目標入手。針對每一個目標領域,都必須問:“為了實現未來的目標,我們現在必須做什么?”為了實現未來的目標,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舍棄過去”。大多數規劃只涉及必須做的新增事物,例如新產品、新流程和新市場,等等。但是,在未來要做一些不同的事情,關鍵在于舍棄不再具有生產性的、陳舊的、過時的東西。因此,做規劃的第一步是要對每項活動、產品、流程或市場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如果我們現在沒有投入資源,我們還會進入嗎?”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接下來就要問:“我們怎樣才能退出,而且是迅速退出?”
系統地舍棄過去本身就是一項規劃——對許多業務都是合適的。它會迫使人們思考和行動,讓企業騰出人員和財力投入新事物,讓人們產生行動的意愿。相反,一項規劃如果只規定要做的新增事物,沒有規定要舍棄的陳舊的老事物,那就不可能取得成果。它會始終是一項規劃,永遠不會成為現實。可是,大多數企業(更多的政府機構)的長期規劃只字不提拋棄過去的決策,也許這就是這些規劃無果而終的主要原因。

我們必須做哪些新的事情:什么時候做
規劃的下一步是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做哪些新的、不同的事情?什么時候做?”每一項規劃都會有這樣一些領域,看起來在這些領域必須做的事情就是更加努力地做現在已經在做的事情。不過,比較明智的做法是假定我們已經在做的事情總是滿足不了未來的需要。但是,“我們必須做哪些事情”還只是問題的一半,同樣重要的還有“什么時候做”,它確定的是何時開始完成新任務。
事實上,每個決策都存在“短期”和“長期”兩個方面。以投資一個鋼鐵廠為例,從方案啟動到可能取得成果的最早時間(開始產出成品鋼)需要5年,那么5年便是這個決策的短期。收回工廠投資及其復利需要20年甚至更長的時間,那么20年便是決策的長期。一個決策的長期,便是證明這個最初決策的正確性需要這個決策繼續保持有效的時間長度,包括在市場、流程、技術和廠址等方面繼續有效。
但是,談論短期規劃和長期規劃是毫無意義的。有一些規劃導致現在的行動,但它們是真正的規劃、真正的戰略決策。有一些規劃談論的是未來的行動,但它們只是一些夢想,甚至是不做思考、不做規劃、不采取行動的托詞。規劃的實質就是在了解決策的未來性的情況下做出當前決策。是未來性決定時間跨度,而不是時間跨度決定未來性。
要經過長時間孕育才能得到結果的事情,就必須盡早開始。因此,長期規劃要求對未來性有所了解:“如果想要在未來實現某個目標,我們現在必須做些什么?如果我們現在不投入資源,哪些事情是做不成的?”
重復一個常用的例子:如果我們知道美國西北部的花旗松需要99年才能生長到用于造紙漿的尺寸,那么為99年以后供應造紙漿用花旗松的唯一辦法就是現在開始栽樹。也許有人會發明一種生長素,但如果我們從事的是造紙業,就絕不能指望這件事情真的發生。如果造紙廠用的原料是花旗松,那么它的規劃就不能只關心20年,而必須考慮99年。
還有一些決策,即使是5年也已長得荒謬可笑。如果我們的業務是整批收購別人虧本銷售的貨物,然后把它們拍賣出去,那么下一周的清倉拍賣就是長期的未來。任何更加長遠的事情,通常都與我們無關。因此,企業及其決策的性質決定了規劃的時間跨度。
時間跨度不是固定的,也不是給定的。在規劃過程中,關于時間的決策本身就是一項承擔著風險的決策,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資源和努力的分配,決定著承擔的風險。推遲決策本身就是一項承擔著風險,而且往往是不可逆轉的決策,這一點無論重復多少遍也不嫌多。在很大程度上,時間決策決定著企業的特點和性質。
總而言之,在戰略規劃中至關重要的是:第一,為了實現目標,要系統地、有目的地進行工作;第二,規劃開始于舍棄過去,并且要把這種舍棄作為實現未來目標所做的系統努力的一部分;第三,我們要尋找實現目標的新途徑,而不是認為更加努力地做同樣的事情就足夠了;最后,我們要深入思考時間因素并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我們必須在什么時候開始工作才能按時取得結果?”
03
一切都要轉化為工作
除非轉化為具體的工作,否則規劃做得再好,也只是一些美好的愿望。一項規劃要經受的檢驗是管理當局是否真的投入資源,并為了在未來取得成果而采取行動。否則,就只有諾言和希望,沒有規劃可言。一項規劃必須通過對管理者提出下面這個問題進行檢驗:“你現在把哪些最優秀的人員投入到了這項工作中?”如果這名管理者反駁說(大多數管理者都會這么說):“我現在不能把最優秀的人員抽出來。只有在他們完成手頭的工作以后,我才能讓他們開始為明天做準備。”這名管理者這么說,實際上是承認自己沒有什么規劃,同時也表明他確實需要一項規劃,因為規劃的目的正是為了揭示稀缺資源——優秀的人員是最稀缺的資源——應該用于何處。
把規劃轉化為工作不僅意味著需要由某個人來承擔這項工作,而且意味著責任、完工期限以及對成果進行衡量,也就是對工作和規劃過程本身的成果的反饋。
在戰略規劃中,衡量會帶來一些嚴峻的問題,特別是概念上的問題。然而,正因為我們衡量什么以及如何衡量決定著大家認為什么是合適的,進而決定著我們看到的是什么以及我們(也包括其他人)做的是什么,所以衡量在規劃過程中是極為重要的。特別重要的是,我們必須設法把各種期望包含在規劃決策中(并且比較清楚地了解在時間和數值方面存在哪些重大偏差),從而及早知道這些期望是否真正能夠實現。否則,我們就無法做規劃。如果沒有反饋,就沒有從實際事件回到規劃過程的自我控制方法。
管理者不能決定自己是否想要做出需要冒風險的長期決策,因為做出這種決策是管理者的天職。管理者只是有權決定自己是負責任的,還是不負責任的做出這種決策,是努力捕捉成功的合理機會,還是純粹靠瞎蒙亂猜。由于決策過程在本質上是一個理性過程,也由于創業型決策的有效性取決于其他人的理解和自愿努力,所以決策方法越是合乎理性、越是有組織、越是以知識而非預言為依據,它就越是負責任的,越有可能生效。不過,決策的最終結果不是知識,而是戰略。它的目標是立即行動。戰略規劃并不是用事實代替判斷,也不是用科學代替管理者。它甚至不會降低管理者的能力、勇氣、經驗、直覺,甚至預感的重要性和作用,這就像生物學和醫學不會降低醫生的這些品質的重要性一樣。相反,系統地開展規劃工作并為其提供知識,強化了管理者的判斷力、領導力和遠見。
本站文章收集整理于網絡,原文出處: ,本站僅提供信息存儲空間服務。如若轉載,請注明出處。






